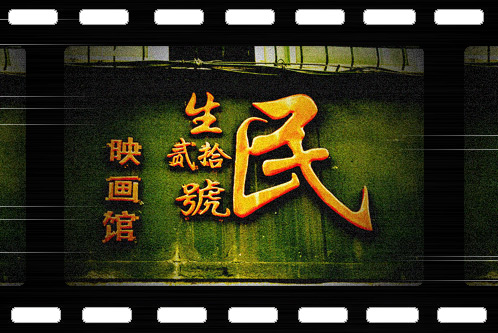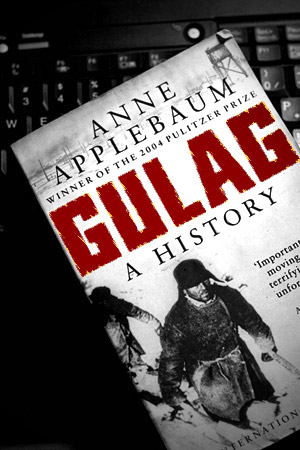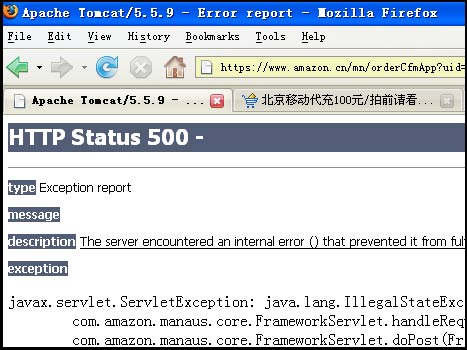他叫束星北,是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不应被忘记的人。
他早年求学欧美,师从惠特克、达尔文、爱丁顿,给爱因斯坦写信讨教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问题。
回国后,他在浙江大学任教,被公认为最杰出活跃的代表:秉性出众,智慧超群,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多年以后,李政道在信中说:“我物理学的基础,都是在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玻尔来中国,见到他,之后回复中国学生关于留学咨询的信件,总是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那样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新政权建立了,束星北来到山东大学。1944年带领学生参与中国研制第一台雷达的他,感觉到了压力:学生徐名冠被“镇反”了,曾经为此呼吁的人纷纷刹车,只有束星北在抗拒。
三反中,有人揪住苏步青在抗战后归还受托管理的浙大财物时,拉下了几条长凳(其实打过招呼)的事情,要做文章。束星北闻听此言,直接闯入节约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质问: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什么东西。说完把主任从凳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打得对方口鼻蹿血,摔出去好几米远。
新山大(系老山大与新政权的华东大学合并而来)的校长华岗,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但也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受到礼遇的束星北,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华岗“用马列主义统摄一切”、“指导科学”的观点。在一次“大课”上,华岗不点名批判了束星北,强调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束星北站起来大喊“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第二”。
对束星北来说,华岗是个好人,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而对华岗来说,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好人的。
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开始了。针对50年的全面苏化,束星北当然有意见:苏联的科学水平是比较差的,像样的科学杂志一本也没有。他积累了多年学识的教科书,也被高教部找人翻译的苏联教材所替代。更要命的,是他当堂折了助教、根正苗红的干部苗子李哲明的面子。李哲明任物理系党支部书记之后,学生忙于与束星北划清界限,他的“队伍”被瓦解了,他的课堂空旷了。他对学生的告诫“政治敷衍过去就行,要好好读书”,也成了他“放毒”的证据。
束星北被孤立了。
下一波,是1954年的“肃反”。当时,他的老友竹可桢、王淦昌为了保护他,专提请教育部在山东大学增设气象研究室(行政上属中科院),而刚刚离开物理系的束星北,也正在气象学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肃反来了,还是因为雷达的事情,他被列为重点,组织上给他配备了“卫兵”,气象学研究室也夭折了。
接着1956年的“苏东波”,1957年,太上皇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刚刚收到党委“道歉”的束星北,发出了远远不同于一般人的声音:他已经意识到,缺乏法制精神,乃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许再广大人民群众中养成认识法律依靠法律捍卫法律的习惯和意识。
在巧夺天工的“阳谋”面前,这样的言论,会得到怎样的下场,是不言自明的。
他的大儿子,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锦州航空部队做教官,却因为父亲的问题,被“黑”了下来:没有工作,没有编制,只能回家当无业游民。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党又发明了“家庭和组织联手配合帮助‘改造’”的法宝。
面对这一切,束星北妥协了,“几千字的‘认罪书’,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耗费了他多少个晚上。”
作为右派分子,他被分配到月子口水库。那是“大跃进”年代,全国疯狂上马的无数水库中,为数不多的优质工程。面对今天已经成为一处景点的水库,人们只能知道,它修建于1958年,建设者是1800名右派,和10000名淮北监狱的犯人(系被“解放”的国民党官兵)。
在月子口,“摘帽”的美好前景,引诱着大家——“互相攻击、检举、揭发、出卖等等,成为了自觉”。
也正是在月子口,束星北感觉到了无力、挫败和苍白:物理学,科学,还有那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早年间的“高高在上”,“靠本事吃饭”的怡然,原来不过是一种虚妄,你连简单的活计都做不好,拖不动小车,扛不起巨石,举不起大锤……喝劳动人民的血汗,吃剥削阶级的残余,却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在月子口的一位“右派”后来说:“月子口似乎对束星北的脉搏把握的非常准,他们似乎本能地知道,技术是束星北的命穴,死死掐住这点不放松,他就不能借技术改造来逃避劳动改造或立场的转变……不过队长还是给了他一次技术改造的机会,那一次,工地断电了,队长派他去检修线路,可是他爬不了电线杆……以后很长时间里,很多地方都拿他做例子,说大教授连个电线都不会接,如何如何”
月子口完工了,束星北回到青岛,被安排到医学院。他已经不复是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的先生,憔悴、浮肿、目光散淡,拄着拐杖,像个泥人。他像个机器人,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比新买的还要干净。
医学院进口了一台丹麦“皇帝”脑电图机,当时属于世界医疗器械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不料,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搁置了两年。院长张立文力排众议,让束星北来修理——他在脑电图室弄了张行军床,吃住都在里面,把机器大卸八块,找到问题,换好零件,再重新装好。“嗡”的一声,机器起死回生了。
从此,他的“修理技能”名身大噪,一些医院纷纷慕名而来,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电子兴奋器、胃镜、比色表,甚至鼓风机、变压器、锅炉、水塔等等,都在他的修理范围内,学院也减免了他打扫厕所的任务,束星北要考虑怎样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更需要的普及性物理学、电工学丛书了”。而他内心深处渴望的“摘帽”,却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据说,是“主管部门”认为他的立场还是有问题。
不过,束星北终于“变”了,在文革中,他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风趣、大度、中交,人们乐于与他下棋、打牌、喝酒、谈私事。在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不太窘迫,这让他的子女都感到吃惊。
但是他内心的向往,是无法泯灭的。1971年元月的头一天,女儿去看他,远远见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的身后,扫出一条长长的路,路两边的雪地上,却是他用扫帚写就的,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看到父亲摇摇晃晃的后背和蓬乱的脑袋,我的泪忽然止不住了。父亲抱着他的外孙只顾在前面走,也不说话,我在后面哭了一路。”
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访问了中国。在会见中,周恩来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譬如介绍些海外才学之士。李政道则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断层”,不是因为没有人才和教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巨大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到了“我的老师束星北”,并希望安排一见。
然而“核心小组”是不容许他们见面的——束星北进京,无论如何不可以,甚至出本市都不行。让李政道来青岛,更是无门——谁知道他到时候会说什么话,再说,束星北家那么破,那么穷,李政道看了会作什么感想!
最终,核心小组决定以身体原因为由,帮束星北推掉了这次会见。
从此师生两分隔,永无见面机会了。
1974年,束星北终于被“摘帽”,1978年,他回到了讲台上,教授四十年前,他在浙江大学的内容。
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长期以来,“不能做事是他心中最大的痛楚”,他要与时间赛跑。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束星北孑然一身,仅以一台计算机(国家拨款100万元他分文未取),一支笔,一摞纸,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计算任务,在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然而,他的身体已经在摧残中垮掉了,1983年9月底,一场小小的风寒,把已经千疮百孔的束星北击倒了。生前嘱托要捐献的遗体,因为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太平间搁置了半年,腐烂不堪,最后草草埋在篮球场的边的双杠下。
这就是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束星北的卷宗,厚厚的八大卷,记录了束星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正是靠着这些卷宗,刘海军先生能全面、立体地为我们复现束星北的生命历程。
更让我吃惊的是,书中收录的各种材料:思想汇报、下级的请示、上级的批示,尤其是各种类型的检举揭发信,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一直很好奇,写下这些信的人,当时、现在,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或许,答案不会有什么新奇罢。
月子口的某位右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二中队的几个小组到农场(机关大队资办)劳动,列队回来,这边刚宣布解散,那边又列队集合。队长和指导员叫出一个队员端着杠子,要我们每个人漱漱口,然后将漱口水突到几个盛满水的脸盆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的时候,手脚立刻寒澈如冰而血液如沸直逼头心。原来是有人告发我们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指导员也不询问证实,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捉贼。人们对这样有辱人格的做法当然不满,确实敢怒不敢言。因为先头有两个人稍一表示出抗拒,就被自己的队友扭住胳膊往里盆里摁。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来到队长面前对他说,我没有偷吃农场的苞谷。队长说,这样可以证明你自己。我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不是这样残酷的方式。队长却说,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方式。这时候,指导员也过来指责我:你要是心里没鬼,还怕接受检查吗?我说,我的良心可以证明我没有偷。指导员说,你的良心要是没有问题,就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开始抗议,我说,我是人,人是有尊严的。指导员一听我说尊严就笑了。他说,我告诉你,月子口没有尊严。队长也跟着喊起来:对,月子口没有尊严。
通过这事,我明白了,我所以总是抵触的症结在哪里。